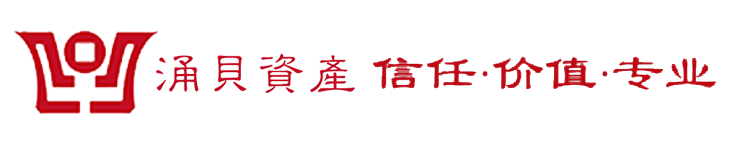当“付费进校”成生意,大学校园该开放吗?
近日,复旦大学、同济大学、上海师范大学、华东理工大学等上海多所高校陆续恢复对公众开放。社交媒体上关于大学校园是否应该完全开放的讨论再度热烈起来。
自疫情防控政策调整之后,仍有一些高校延续了过去三年的封闭管理政策。尽管今年初,国内一些高校恢复了部分人员出入校园的权限,但仅限校友,一些学校扩大至“学生亲友”的范畴,绝大部分的外来人员被阻隔在高墙之外。
“朋友们聚会还是想去学校看看。”中国传媒大学校友袁华对界面教育表示,近日他通过学校APP线上注册申请进校,但不知为何显示未成功,“可能方法不对,试了很多次。”
袁华表示,学校不对外开放,受影响较大的可能是住在学校附近的居民。袁华于2017年毕业,专门选择在中传附近租房,“那个时候我就想,没事儿去学校的食堂吃吃饭,打打球,享受一下学校的便利。”后来赶上疫情,学校封闭后,袁华也换了租房地。
科幻作家韩松也在这上面栽了跟头。今年3月底,武汉大学举办130周年校庆活动,作为校友的韩松想回母校看看,但“因为预约时间失误,且不能修改,完美错过武大赏樱,预约成功的记录似乎不会消除,因此也不能再预约。”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段经历,不少网友伸出援手,表示可以带他进去。
还有一些人从中发现“商机”,“付费入校”成了一种“商业模式”。
“武大免预约代入校,任意校门都可以,进门确认收货付款,4人以上有优惠。”在咸鱼上,一位自称“武汉大学在校生”的卖家售卖相关产品。其动态页面显示,五月以来已售出“带入校”商品近30笔,每单收费在24-100元不等。
除此之外,还有一些通过种种渠道拿到学生卡、校友卡的“黄牛”,在小红书、微博等社交平台发布“付费进校”的广告,“收费不是最低,150元/人,能接受的私(聊),不墨迹。”在评论下方,有不少学生举报并予以抵制,“大家不要给黄牛送钱”。
对于学校来说,难以验证来访人员与申请人员是否是真实的亲友关系,这为付费进校提供了牟利空间。毫无疑问的是,这种违法违规行为应该得到坚决抵制。但滋生这种行为背后,还是校园封闭与公众想入校参观旁听的需求,难以得到匹配和平衡。
关于大学校园是否该开放,舆论对此意见不一。
支持者认为,高校应该恢复疫情之前的开放措施,“海纳百川”、“兼容并包”——这些为人们所熟知的大学校训都在强调开放理念,作为物理屏障的大学校门,原本就是第一个不该关闭的。
此外,这种开放不应只局限于物理空间意义上,更重要的是公办高校的各类资源理应与社会共享,可以为许多人创造学习机会。从这一意义上说,大学不是、也不应该是封闭的象牙塔,彼此孤立的大学就失去了大学本身的应有之义。
也有反对者认为,现在全面恢复还不是时候,各地还有“二阳”病例,且有增多趋势。二是资源分配问题,简单放开必然面临校园资源挤兑的问题,如此一来,如果连本校师生的便利都保障不了的话,一味放开有何意义。最后,由于社会人员情况复杂,也会对校园师生带来安全隐患。
事实上,早在新冠疫情之前,部分知名高校就已开始限制社会人员入校,并引发过公众对大学校园开放问题的关注和讨论。
2017年,中山大学因“限制校外人员入校”的规定引发争议,该校校友认为此举有违中山大学一向的开放精神,希望学校公开“限外令”依据。彼时,中山大学回应,此前有不利于学校治安的事件发生,“限外令”是出于安保考虑。
同期,北大、清华等高校也对社会人员入校有所限制。2018年,北大清华双双推出校园参观预约系统,对外来进入人员数量和入校时间有着明确限制。再后来,三年疫情,高校大门紧闭,不仅外来人员无法进入,就连校内学生出来也困难重重。
“在社会已经全面恢复到疫情之前的生活秩序时,高校再以疫情防控为由,不恢复向社会公众开放,是站不住脚的。”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对界面教育表示,公办高校的资源属于全社会,理应向社会开放,让社会公众共享公共教育资源。
但熊丙奇也提到,高校的首要任务是办学,培养人才。校园开放的前提是不影响学校的教育教学秩序。为此,高校是否向社会开放、怎么开放,应该充分听取全校师生和社区居民的意见,进行科学、民主决策。
在谈及校园开放时,国内舆论通常会引用“国外大学没有围墙、和社区融合在一起”的例子。但在熊丙奇看来,国外大学的开放也不是一概而论的,有的校园面积小、校园周边社区治安比较复杂的学校,也是不向社会公众开放的。
即使融入社区的大学校园,有的图书馆、体育馆等场馆也有门禁系统,非本校师生并不能自由进入。学校对外开放的措施,是学校董事会,在听取师生和社区居民意见后做出的,因此,对于是否开放、开放的程度以及开放措施,师生和社区居民存在一定共识。
“在我国,有形的校园围墙的开放与关闭,尚未能制定明确的制度规范与有效举措。”2020年4月,陕西学前师范学院教师张强发表的《公立大学校园开放的法理、学理与治理》一文曾指出。
究其根源,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。首先,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学扩招,造成了高等教育资源的紧缺,公众的进入进一步造成资源紧张局面的恶化,校内师生与校外人员之间的矛盾时有发生。其次,民众在参观校园过程中缺乏素质的表现,引起了校内师生的反感与排斥。
张强认为,公立大学的校园开放问题涉及公物利用的法理、大学价值的学理以及利益相关者的治理等层面。立足公物理念,需要澄清公立大学校产的所有权与使用权,为校园开放的正当性提供法理支持。
学府与社会之间的互动,依据学理的要求,应当引领区域文化风气,满足民众的精神文化需求。最后,通过政府的支持、学校的引导、以及民众的参与,实现有效的校园治理,最终在有序开放的基础上实现大学功用的发挥与社会文化的改善。
熊丙奇认为,针对开放可能带来的安全管理问题,学校可以制订校园开放管理规定,招募学生以及社区志愿者参与开放后的校园秩序维护。
针对开放带来的市民与学生“抢”体育馆、图书馆等场馆资源的问题,可以引入第三方机构,建立开放资源管理平台,选择合适的时段,向社区居民开放。而且,这一开放资源管理平台,还可以把所有学校、社区资源整合在一起,向社会公众开放,并提高开放管理效率。
就当下的校园开放而言,高校应该顺应社会公众要求开放的呼声,将校园开放恢复到疫情前的程度。同时,在听取师生和社区居民意见基础上,梳理可以向社会开放的校内资源,建立校园开放的长效机制。
关键词:涌贝资产、大学校园、社区资源